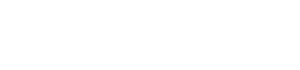个人简介
人物简介
张瑞瑾,水利科学家和教育家。在高等教育中,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河流泥沙及治河工程本科专业。长期致力于河流泥沙运动基本理论和实际工程应用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就得出黄河年均产沙量为15亿吨的科学数据;50年代提出泥沙沉速和泥沙起动等计算公式;60年代提出水流挟沙力公式;70年代,在长江葛洲坝设计中,提出了解决船闸上、下游引航道泥沙淤积的基本途径;80年代曾担任三峡工程泥沙研究协调组组长,为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研究解决作出了贡献。
张瑞瑾,1917年1月15日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39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毕业论文题目为《永定河治本计划与美国密西密河防洪计划的比较研究》,全文用英文写成,八万余字。这是他接触治河及泥沙问题的开始。当时,正处在日寇入侵,国家危亡的艰难时刻,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在全系举行的送别会上,他怀着忧国忧民以及对日寇的愤怒,在《踏莎行·留别》的词中写道:“翠锁凌云,水盈大渡,眼嘘得殆将飞去。念三子,自顾平庸,破碎江山怎么补! 巴峡风腥,嘉州月苦,感君送别痛无语。长空暗淡失归程,旧山玉宇侵獠虏。”
大学毕业后,去重庆中央大学工学院航空机械研究班学习。先后在重庆、南京中央水利实验处工作。1945年5月公费留美学习、进修。1947年回到母校武汉大学任教,历任校副教务长、工学院副院长、水利学院院长等职。1954年底,国家对大学进行院系调整时,组建成立了武汉水利学院,他被任命为副院长、党委常委。1978年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院长。1983年10月被国务院任命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名誉院长。
1949年4月加入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中国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195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先后在许多学术团体和机构中任职,是我国河流泥沙研究与教育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历任中国水利学会常务理事、名誉理事,中国水利学会泥沙专业委员会第一届主任委员,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组织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水利学组成员,国家科委学科规划委员会水利学科组副组长,湖北省科协副主席,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水利电力部高等学校水利水电类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工科学校基础课力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治黄规划组副组长,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研究协调小组组长,三峡工程研究及论证委员会泥沙专家组顾问,水利部第一届技术委员会顾问等职务。在这些工作岗位上,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1959年,他曾以中国教育工作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去越南帮助筹建越南水利学院和越南水利科学研究院。1974年,他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赴巴黎参加国际水文十年总结大会。1975 年,他以中国国家水文委员会主席身份赴巴黎出席国际水文计划会议,在这次会上,中国当选为国际水文计划三十个理事国之一。1980年第一次国际河流泥沙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他担任组织委员会副主席,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初承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之一,成为以后这一领域每三年一次系列国际会议的开端。1983年第二次国际河流泥沙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他担任组织委员会副主席兼论文评审委员会主席,鉴于我国在这个领域研究中取得的突出成就,这次会上与会各国代表同意将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设在中国,该中心于1984年在北京成立。1978年他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他参加的葛洲坝二江、三江工程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开拓和发展了中国的泥沙运动基本理论
张瑞瑾长期致力于河流泥沙运动基本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1946年在南京中央水利实验处任职期间,他通过对关中、包惠渠和花园口等地的实地观测,分析大量资料,弄清了黄河的泥沙,提出黄河每年输沙量为15亿多吨的科学数据。20世纪50年代,他提出了水流中泥沙沉降速度计算公式,该公式适用范围广,对滞性区、过渡区和紊流区均适用;根据不同颗粒粒径泥沙在河床床面上的受力特点,提出了水流作用下河床上散粒体泥沙和黏性沙起动临界流速统一计算公式;改进了河流中悬移质含沙量沿垂线分布的Rouse公式,提出的新的计算式克服了Rouse公式存在的水面含沙量为零、河底含沙量为无穷大的缺陷,与实测资料吻合更好。60年代,在对原苏联学者提出的悬移质运动重力理论进行系统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悬移质运动“制紊假设”,并广泛搜集和认真分析了大量有关长江、黄河等我国江河渠系及试验室资料,最终提出建立了悬移质水流挟沙力公式,该公式已成为河流动力学中经典公式之一,在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中得到广泛应用,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该成果获得全国重大科学成果奖,并被授予“在科学技术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先进工作者”称号。70年代,他在黄河流域大量野外调查和研究基础上发表了高含沙水流方面的研究成果,揭示了高含沙水流不同于一般含沙水流的运动机理,他是我国最早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之一。80年代,他提出了河工模型变态指标,推动了变态河工模型理论的发展。
张瑞瑾教授1961年编著的《河流动力学》,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河流泥沙学科领域内的高校教材和重要科技书籍,在此之前,国际上只有前苏联出版过两本这方面的著作,此书反映了当时该学科的国际前沿学术水平,为以后我国河流泥沙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根治黄河呕心沥血
黄河,我国的第二大河,它流经九省(自治区),造就了广阔的华北大平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它又是闻名世界的多沙河流。据史记载,黄河大决口,就有26次之多。造成这些灾害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多沙。要根治黄河,必须从治沙着手。早在20世纪40年代,张瑞瑾就开始了这一研究,通过分析大量资料,指出黄河每年输沙量为15 亿多吨的科学数据。
20世纪60年代初期,根据毛泽东“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治黄工作会议。会上,周总理说:陕北的人民抚育过我们,可是至今,他们的生活仍很艰苦,为了提高黄河两岸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加速治理黄河。会后,作为“治黄规划工作组”副组长,为制订治黄规划,他踏遍了黄河的高原峡谷,在人烟稀少、山路崎岖的地区,骑着小毛驴进行查勘。他把调查研究黄河的历史和现状放在首位,组织师生,多次对黄河进行查勘、规划和研究,既治黄又育人。他竭力呼吁:黄河安危,事关重大,必须加强研究,及早采取措施。在1977年召开的全国科学规划会上,他指出,“黄河病在多沙,中游为多沙之源。擒贼先擒王。治黄必须突出中游,狠抓主要产沙区陕北、晋西北、陇东等十万平方千米的水土保持和支流流域治理是治黄的笼木途径。”他根据黄河下游实施“宽河固堤”多年的经验,以及下游河南段河虽然宽而堤难守,山东段槽虽定而堤易溢,上段河势变化无常,下段泄洪能力过小的特点,认为黄河下游河道治理一个值得考虑的方针是“宽滩窄槽”。实现这一方针,包括护滩定槽(重点在高村以上)、平滩护岸、滩面杜串以及退堤扩滩(位山以下)等具体措施。在治理过程中,治导线必须因地制宜,一般以蜿蜒型为主。修建治理工程(即所谓“控导工程”)必须抓住各河段有利时机,为实现利用凹岸导流,做好“迎、顶、送”(即所谓“上平、下缓、中间陡”)建筑物群。
1982年,在黄河小浪底工程论证会上,他就该工程在我国水资源跨流域调配中的作用发表了重要意见,指出:从远景来看,由于我国水资源分布的总的轮廓是:东南丰、西北欠;南雨早、北雨迟;年内分配不均,年际变幅甚大;水能偏富西南;黄河流域的干旱指数多在1.5~10之间,海河、滦河流域的干旱指数多在2.0以下,京、津地区的干旱指数多在1.5~2.0之间。因而,引黄北济京、津,是以匮乏济不足,至少是以不足济不足。从近期来看,如果作为应急之需,临时从黄河引水济津,过去已经做过,今后也难免还要做,但用不着指望小浪底工程。至于引江北济京、津,从长远规划看,是以有余济不足,在规划上是合理的。在完成东线引水北调之前,短期中临时解决京、津缺水问题,以先就近从海河、滦河打主意,再从黄河找主意(不靠小浪底水库)为宜。
为开发长江殚精竭虑
197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另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就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宏伟工程,万里长江第一坝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上马了。顿时,大江南北的技术力量,纷纷调动,云集宜昌。张瑞瑾已在该年早些时候的6月来到宜昌。此前他正在湖北省长阳县平洛公社劳动、接受审查批斗。一天,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亲自要通平洛公社的电话,点名要他参加一个重要水利工程建设。接到电话后他挑着行李匆匆赶往宜昌。
三江船闸引航道泥沙淤积问题,是葛洲坝工程三大技术难题之一,也是关系到该项工程成败的首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重大技术问题,多少人在日思夜想,多少人在辗转难眠。一个又一个方案的提出,一次又一次激烈的争论。当时存在两种观点:一种主张“静水不淤”,另一种主张“常流水”,一时间,众说纷纭。他当时还属于被批判对象,每次开会,都得忍受“专家”、“教授” 的冷嘲热讽,更重要的是政治压力。但他时刻铭记周总理的嘱咐:“葛洲坝工程如果出问题,将来是要写入党史的”。他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本着一个科学家应有的科学态度,坚持真理。他亲自组织人马,查勘现场,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仔细分析各家观点,详细研究论争的要点。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首先需要摸清天然情况下水沙运动规律,为此他深入到祖祖辈辈生活在长江边的老农民中调查,和在长江航行几十年的老船长以及在南津关摆渡几十年的老船工交朋友。为弄清葛洲坝坝前基岩老虎堆对分流的影响,他乘着小划子,到现场查勘,岩堆不大,但很陡,还长满了青苔,他赤着脚连上几次,因太滑没有成功。同志们劝他不要上了,他咬着牙:“我爬也要爬上去”。
为了弄清船闸上、下游水流状态对泥沙问题的影响,他率领科研组,先后调查了广东、广西、湖南等地的二十多座船闸,特别是对失败了的船闸,作了详细研究。写出的“关于船闸淤积问题的调查报告”对指导葛洲坝工程枢纽布置、解决引航道泥沙淤积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还主持了葛洲坝工程工地正态泥沙模型试验。与其他同志一道,通过控制水中钙、镁离子含量的方法,成功地采用了粒径极细的(中值粒径约0.01mm)酸性白土粉作为模型沙模拟了悬移质泥沙的冲淤变化。这比当时国际上采用的最小粒径为0.1mm 的模型沙,整整小一个数量级。通过大量的研究,结合分析长江水量丰富、含沙量中等的特殊条件,终于找到了解决引航道泥沙淤积问题的基本途径——“静水过船,动水冲沙”。具体措施是:在船闸附近不布置电站,只布置泄量足够的若干孔冲沙闸(全部冲沙闸均可利用宣泄特大洪水所必需的泄水闸构成,不用另建),这些冲沙闸,除了在特大洪水时期(此时不通航)开启以外,平时关闭,使船闸上下游引航道中基本上保持静水,以利船只和船队顺利过闸,这样,引航道中势必发生淤积。等淤积发展到一定程度接近碍航时(以及其他认为必需或便利的时候),启用冲沙闸,使上下游引航道中产生足够的流速,将淤沙冲走。此时船只暂停过闸。在冲沙的时候,会有一些死角为水流所不及,可视情况铺以机械清淤措施。模型试验表明,每年冲沙所需的总时间一般少于3~5天。
在工地几年,他终因过度紧张劳累而身患重病,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时刻关心我国大江大河的治理开发工作。
1981年1月4日,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江截流胜利合龙! 奔腾不息的长江,第一次服从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当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登载:葛洲坝三江航道冲沙闸启动冲沙成功。10月份的两次冲沙,共用了22小时就清除了由于这次大洪水淤积在引航道中的280 万立方米泥沙,冲沙效率达89%,下游航道河床平均冲深3.05米,达到通航要求。实践与科学研究的结果完全吻合。作为从一开始就直接参加该工程建设的泥沙方面的主要专家,看到这些报道后,张瑞瑾实在太激动了。在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科技成果交流会期间,他拖着病情刚有好转的身子,来到葛洲坝,面对浩浩荡荡的长江,为寄胸怀,以诗言志:“大江今日喜初妆,久病新瘥来贺忙。成城众志堪入史,放眼云天路正长。”
1983年,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提上日程。在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会上,他作了“兴建三峡工程有待解决的泥沙问题”的发言,阐述了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复杂性、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可能性。会议总结时,宋平宣布:“水电部委托张瑞瑾负责(长江科学院陈济生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谢鉴衡协助)及早在武汉召开三峡工程泥沙试验研究工作协调会议”。他为三峡工程泥沙试验研究方案的拟定和国内各单位间的合理分工等作了大量工作,为以后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研究解决铺平了道路。1985年起,因身体原因,他改任三峡工程研究及论证委员会泥沙专家组顾问。
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时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他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教育学会,并支持进步的学生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党的教育事业。1954 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以他为主要领导成员,组建成立了武汉水利学院(此后先后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并成为首批全国重点大学。2000年,武汉水利电力大学与原武汉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和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成新的武汉大学前,该学校已成为国内外水利电力领域著名的大学,为我国建设事业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水利电力方面的高级科技人才,推动和促进了我国水利电力事业的发展。根据我国自然条件的特点及经济建设的需要,他还在1958年创办了世界上唯一的河流泥沙及治河工程专业,并建设起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河流泥沙研究基地。
在三十多年的高校领导工作中,他8小时上班时间完全投入在办学和教育事业上,而把所有能利用的业余时间全部用在了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上。他善于抓主要矛盾,善于抓大事,把主要精力都花在党的教育事业上,同时又不放弃科研工作。他治学态度非常严谨。他既精通英、俄、德等外语,又具有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他在文字上的严格精炼是众所周知的。在科学研究中,他善于运用哲学思想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他在业务自传中写道:“从事业务工作,同干党的行政工作一样,指导思想如何是十分重要的。搞科学理论研究如此,解决重大技术问题也是如此。50年代我注意以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为主系统读了一些马、恩、列、斯的哲学著作,感到有如启蒙教育,受益匪浅,从思想深处深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事半功倍的锐利武器。”他常说:“如果一辈子想为人民多做点有益的事,就要一辈子学习辩证法”。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 年代,他编著的《水力学》和《河流动力学》等教科书中,既反映了当时国际学术水平,又纳入大量个人研究成果,其中许多精辟的论述和分析,无不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并以立论严谨、说理透彻而深受广大教学科研工作者的褒赞。
作为学校领导,对待下级和中青年知识分子,他循循善诱,言传身教。他培养的学生已遍布全国,桃李满天下。有的已成为国内外很有影响的专家教授,有的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更多的成为我国水利电力事业的中坚力量。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多次住院,行动非常不便。可是,他依靠药物的支持,利用每次服药后药物作用发挥的时间,主持会议,与人谈话,指导研究生,深入实验室,用颤抖的手写讲稿,编教材。仅论文和有关报告,就有30余万字。同时,他还频繁奔波于北京、南京、郑州、宜昌等地,参加各种重要会议。仅1981 年7月到1982年8月这段时间,出席全国性专业及有关会议共9次计100多天,还不包括他当时在校内所担任的党和行政工作。不说一个疾病缠身的老人,就是一个体格健壮的人,要完成这么多工作,没有一种拼搏精神,是不可能办到的。
(张小峰)
简 历
1917年1月15日 出生于湖北巴东。
1939年7月 毕业于武汉大学工学院。
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 中央大学工学院航空机械研究班学习。
1940年3月至1943年3月 中央水利实验处(重庆)先后任技佐、技士、副研究员。
1943年3—8月 恩施湖北省银行水利技术专员。
1943年9月至1944年1月 日寇进攻战事吃紧,辞职在家。
1944年2—7月 重庆乡村建设育才学院任水利科讲师。
1944年9月至1946年8月 国民政府水利委员会(重庆南京)任副工程师(在职期间曾考取公费留美,于1945年5 月出国,1946年7月回国)。
1946年8月至1947年10月 中央水利实验处(南京)研究员。
1947年11月至1954年11月 武汉大学教授,校副教务长、工学院副院
长、水利学院院长、校党组成员。
1954年11月至1978年10月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副院长、党委常委。
1978年10月至1983年10月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院长兼学院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主席。
1983年10月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名誉院长。
1998年12月21日 逝世于武汉。
主 要 论 著
1 张瑞瑾. 河流动力学. 北京:中国工业出版社,1961.
2 张瑞瑾. 河流泥沙动力学.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
3 Zhang Ruijin,Xie Jianheng. Sediment Research in China. 1992.
4 张瑞瑾. 黄河泥沙冲积数量之分析. 水利,1947,15(1).
5 张瑞瑾. 悬移泥沙在二度等速明流中的平衡情况下是怎样分布的. 新科学,1950(3).
6 张瑞瑾. 关于费里堪诺夫的明渠挟沙力流的重力理论. 武汉水利学院学报,1957(1).
7 张瑞瑾. 长江中下游水流挟沙力研究. 泥沙研究,1959,4(2).
8 张瑞瑾. 长江中下游水流挟沙力研究(续). 泥沙研究,1959,4(2).
9 张瑞瑾. 论重力理论兼论悬移质运动过程. 水利学报,1963(3).
10 张瑞瑾. 论环流结构与河道演变的关系. 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土木、建筑、水利版),1964(1).
11 张瑞瑾,等. 评爱因斯坦关于推移质运动的理论兼论推移质运动过程.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院报,1965(3-4).
12 张瑞瑾. 中国水利建设中的水文工作. 中国科学,1975(1).
13 张瑞瑾. 静水过船,动水冲沙.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报,1975(1).
14 张瑞瑾. 高含沙量水流流性初探.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报,1978(1).
15 张瑞瑾. 对黄河中游的认识.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报,1979(4).
16 张瑞瑾. 关于根治黄河的关键途径问题.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报,1979(4).
17 张瑞瑾. 关于河道挟沙水流比尺模型相似律问题.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报,1980(3).
18 张瑞瑾等. 蜿蜒型河段演变规律探讨//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上海:光华出版社,1980.
19 张瑞瑾.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泥沙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中国水利,1981(4).
20 Zhang Ruijin,Sediment Problems of the Gezhouba Water Control Project on the Yangtze River,Paper No. 001,Series of Research Reports—WIHEE,May 1982.
21 张瑞瑾,谢鉴衡. 葛洲坝枢纽坝区泥沙与河势规划问题//葛洲坝枢纽工程科技成果交流会文件,1981.
22 张瑞瑾,等. 论河道水流比尺模型变态问题//第二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3.
23 张瑞瑾,陈济生,谢鉴衡. 三峡工程前阶段泥沙科研工作汇报提纲// 长江三峡工程泥沙研究文集. 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89.
24 张瑞瑾. 张瑞瑾论文集.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6.
人物简介
张瑞瑾,水利科学家和教育家。在高等教育中,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河流泥沙及治河工程本科专业。长期致力于河流泥沙运动基本理论和实际工程应用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就得出黄河年均产沙量为15亿吨的科学数据;50年代提出泥沙沉速和泥沙起动等计算公式;60年代提出水流挟沙力公式;70年代,在长江葛洲坝设计中,提出了解决船闸上、下游引航道泥沙淤积的基本途径;80年代曾担任三峡工程泥沙研究协调组组长,为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研究解决作出了贡献。
张瑞瑾,1917年1月15日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39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毕业论文题目为《永定河治本计划与美国密西密河防洪计划的比较研究》,全文用英文写成,八万余字。这是他接触治河及泥沙问题的开始。当时,正处在日寇入侵,国家危亡的艰难时刻,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在全系举行的送别会上,他怀着忧国忧民以及对日寇的愤怒,在《踏莎行·留别》的词中写道:“翠锁凌云,水盈大渡,眼嘘得殆将飞去。念三子,自顾平庸,破碎江山怎么补! 巴峡风腥,嘉州月苦,感君送别痛无语。长空暗淡失归程,旧山玉宇侵獠虏。”
大学毕业后,去重庆中央大学工学院航空机械研究班学习。先后在重庆、南京中央水利实验处工作。1945年5月公费留美学习、进修。1947年回到母校武汉大学任教,历任校副教务长、工学院副院长、水利学院院长等职。1954年底,国家对大学进行院系调整时,组建成立了武汉水利学院,他被任命为副院长、党委常委。1978年任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院长。1983年10月被国务院任命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名誉院长。
1949年4月加入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中国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195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先后在许多学术团体和机构中任职,是我国河流泥沙研究与教育工作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历任中国水利学会常务理事、名誉理事,中国水利学会泥沙专业委员会第一届主任委员,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组织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水利学组成员,国家科委学科规划委员会水利学科组副组长,湖北省科协副主席,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水利电力部高等学校水利水电类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工科学校基础课力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治黄规划组副组长,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研究协调小组组长,三峡工程研究及论证委员会泥沙专家组顾问,水利部第一届技术委员会顾问等职务。在这些工作岗位上,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1959年,他曾以中国教育工作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去越南帮助筹建越南水利学院和越南水利科学研究院。1974年,他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赴巴黎参加国际水文十年总结大会。1975 年,他以中国国家水文委员会主席身份赴巴黎出席国际水文计划会议,在这次会上,中国当选为国际水文计划三十个理事国之一。1980年第一次国际河流泥沙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他担任组织委员会副主席,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初承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之一,成为以后这一领域每三年一次系列国际会议的开端。1983年第二次国际河流泥沙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他担任组织委员会副主席兼论文评审委员会主席,鉴于我国在这个领域研究中取得的突出成就,这次会上与会各国代表同意将国际泥沙研究培训中心设在中国,该中心于1984年在北京成立。1978年他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他参加的葛洲坝二江、三江工程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开拓和发展了中国的泥沙运动基本理论
张瑞瑾长期致力于河流泥沙运动基本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1946年在南京中央水利实验处任职期间,他通过对关中、包惠渠和花园口等地的实地观测,分析大量资料,弄清了黄河的泥沙,提出黄河每年输沙量为15亿多吨的科学数据。20世纪50年代,他提出了水流中泥沙沉降速度计算公式,该公式适用范围广,对滞性区、过渡区和紊流区均适用;根据不同颗粒粒径泥沙在河床床面上的受力特点,提出了水流作用下河床上散粒体泥沙和黏性沙起动临界流速统一计算公式;改进了河流中悬移质含沙量沿垂线分布的Rouse公式,提出的新的计算式克服了Rouse公式存在的水面含沙量为零、河底含沙量为无穷大的缺陷,与实测资料吻合更好。60年代,在对原苏联学者提出的悬移质运动重力理论进行系统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悬移质运动“制紊假设”,并广泛搜集和认真分析了大量有关长江、黄河等我国江河渠系及试验室资料,最终提出建立了悬移质水流挟沙力公式,该公式已成为河流动力学中经典公式之一,在科学研究和工程设计中得到广泛应用,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该成果获得全国重大科学成果奖,并被授予“在科学技术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先进工作者”称号。70年代,他在黄河流域大量野外调查和研究基础上发表了高含沙水流方面的研究成果,揭示了高含沙水流不同于一般含沙水流的运动机理,他是我国最早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之一。80年代,他提出了河工模型变态指标,推动了变态河工模型理论的发展。
张瑞瑾教授1961年编著的《河流动力学》,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河流泥沙学科领域内的高校教材和重要科技书籍,在此之前,国际上只有前苏联出版过两本这方面的著作,此书反映了当时该学科的国际前沿学术水平,为以后我国河流泥沙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根治黄河呕心沥血
黄河,我国的第二大河,它流经九省(自治区),造就了广阔的华北大平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它又是闻名世界的多沙河流。据史记载,黄河大决口,就有26次之多。造成这些灾害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多沙。要根治黄河,必须从治沙着手。早在20世纪40年代,张瑞瑾就开始了这一研究,通过分析大量资料,指出黄河每年输沙量为15 亿多吨的科学数据。
20世纪60年代初期,根据毛泽东“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治黄工作会议。会上,周总理说:陕北的人民抚育过我们,可是至今,他们的生活仍很艰苦,为了提高黄河两岸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加速治理黄河。会后,作为“治黄规划工作组”副组长,为制订治黄规划,他踏遍了黄河的高原峡谷,在人烟稀少、山路崎岖的地区,骑着小毛驴进行查勘。他把调查研究黄河的历史和现状放在首位,组织师生,多次对黄河进行查勘、规划和研究,既治黄又育人。他竭力呼吁:黄河安危,事关重大,必须加强研究,及早采取措施。在1977年召开的全国科学规划会上,他指出,“黄河病在多沙,中游为多沙之源。擒贼先擒王。治黄必须突出中游,狠抓主要产沙区陕北、晋西北、陇东等十万平方千米的水土保持和支流流域治理是治黄的笼木途径。”他根据黄河下游实施“宽河固堤”多年的经验,以及下游河南段河虽然宽而堤难守,山东段槽虽定而堤易溢,上段河势变化无常,下段泄洪能力过小的特点,认为黄河下游河道治理一个值得考虑的方针是“宽滩窄槽”。实现这一方针,包括护滩定槽(重点在高村以上)、平滩护岸、滩面杜串以及退堤扩滩(位山以下)等具体措施。在治理过程中,治导线必须因地制宜,一般以蜿蜒型为主。修建治理工程(即所谓“控导工程”)必须抓住各河段有利时机,为实现利用凹岸导流,做好“迎、顶、送”(即所谓“上平、下缓、中间陡”)建筑物群。
1982年,在黄河小浪底工程论证会上,他就该工程在我国水资源跨流域调配中的作用发表了重要意见,指出:从远景来看,由于我国水资源分布的总的轮廓是:东南丰、西北欠;南雨早、北雨迟;年内分配不均,年际变幅甚大;水能偏富西南;黄河流域的干旱指数多在1.5~10之间,海河、滦河流域的干旱指数多在2.0以下,京、津地区的干旱指数多在1.5~2.0之间。因而,引黄北济京、津,是以匮乏济不足,至少是以不足济不足。从近期来看,如果作为应急之需,临时从黄河引水济津,过去已经做过,今后也难免还要做,但用不着指望小浪底工程。至于引江北济京、津,从长远规划看,是以有余济不足,在规划上是合理的。在完成东线引水北调之前,短期中临时解决京、津缺水问题,以先就近从海河、滦河打主意,再从黄河找主意(不靠小浪底水库)为宜。
为开发长江殚精竭虑
197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另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就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宏伟工程,万里长江第一坝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上马了。顿时,大江南北的技术力量,纷纷调动,云集宜昌。张瑞瑾已在该年早些时候的6月来到宜昌。此前他正在湖北省长阳县平洛公社劳动、接受审查批斗。一天,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亲自要通平洛公社的电话,点名要他参加一个重要水利工程建设。接到电话后他挑着行李匆匆赶往宜昌。
三江船闸引航道泥沙淤积问题,是葛洲坝工程三大技术难题之一,也是关系到该项工程成败的首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重大技术问题,多少人在日思夜想,多少人在辗转难眠。一个又一个方案的提出,一次又一次激烈的争论。当时存在两种观点:一种主张“静水不淤”,另一种主张“常流水”,一时间,众说纷纭。他当时还属于被批判对象,每次开会,都得忍受“专家”、“教授” 的冷嘲热讽,更重要的是政治压力。但他时刻铭记周总理的嘱咐:“葛洲坝工程如果出问题,将来是要写入党史的”。他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本着一个科学家应有的科学态度,坚持真理。他亲自组织人马,查勘现场,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仔细分析各家观点,详细研究论争的要点。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首先需要摸清天然情况下水沙运动规律,为此他深入到祖祖辈辈生活在长江边的老农民中调查,和在长江航行几十年的老船长以及在南津关摆渡几十年的老船工交朋友。为弄清葛洲坝坝前基岩老虎堆对分流的影响,他乘着小划子,到现场查勘,岩堆不大,但很陡,还长满了青苔,他赤着脚连上几次,因太滑没有成功。同志们劝他不要上了,他咬着牙:“我爬也要爬上去”。
为了弄清船闸上、下游水流状态对泥沙问题的影响,他率领科研组,先后调查了广东、广西、湖南等地的二十多座船闸,特别是对失败了的船闸,作了详细研究。写出的“关于船闸淤积问题的调查报告”对指导葛洲坝工程枢纽布置、解决引航道泥沙淤积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还主持了葛洲坝工程工地正态泥沙模型试验。与其他同志一道,通过控制水中钙、镁离子含量的方法,成功地采用了粒径极细的(中值粒径约0.01mm)酸性白土粉作为模型沙模拟了悬移质泥沙的冲淤变化。这比当时国际上采用的最小粒径为0.1mm 的模型沙,整整小一个数量级。通过大量的研究,结合分析长江水量丰富、含沙量中等的特殊条件,终于找到了解决引航道泥沙淤积问题的基本途径——“静水过船,动水冲沙”。具体措施是:在船闸附近不布置电站,只布置泄量足够的若干孔冲沙闸(全部冲沙闸均可利用宣泄特大洪水所必需的泄水闸构成,不用另建),这些冲沙闸,除了在特大洪水时期(此时不通航)开启以外,平时关闭,使船闸上下游引航道中基本上保持静水,以利船只和船队顺利过闸,这样,引航道中势必发生淤积。等淤积发展到一定程度接近碍航时(以及其他认为必需或便利的时候),启用冲沙闸,使上下游引航道中产生足够的流速,将淤沙冲走。此时船只暂停过闸。在冲沙的时候,会有一些死角为水流所不及,可视情况铺以机械清淤措施。模型试验表明,每年冲沙所需的总时间一般少于3~5天。
在工地几年,他终因过度紧张劳累而身患重病,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时刻关心我国大江大河的治理开发工作。
1981年1月4日,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江截流胜利合龙! 奔腾不息的长江,第一次服从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当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登载:葛洲坝三江航道冲沙闸启动冲沙成功。10月份的两次冲沙,共用了22小时就清除了由于这次大洪水淤积在引航道中的280 万立方米泥沙,冲沙效率达89%,下游航道河床平均冲深3.05米,达到通航要求。实践与科学研究的结果完全吻合。作为从一开始就直接参加该工程建设的泥沙方面的主要专家,看到这些报道后,张瑞瑾实在太激动了。在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科技成果交流会期间,他拖着病情刚有好转的身子,来到葛洲坝,面对浩浩荡荡的长江,为寄胸怀,以诗言志:“大江今日喜初妆,久病新瘥来贺忙。成城众志堪入史,放眼云天路正长。”
1983年,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提上日程。在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会上,他作了“兴建三峡工程有待解决的泥沙问题”的发言,阐述了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复杂性、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可能性。会议总结时,宋平宣布:“水电部委托张瑞瑾负责(长江科学院陈济生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谢鉴衡协助)及早在武汉召开三峡工程泥沙试验研究工作协调会议”。他为三峡工程泥沙试验研究方案的拟定和国内各单位间的合理分工等作了大量工作,为以后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的研究解决铺平了道路。1985年起,因身体原因,他改任三峡工程研究及论证委员会泥沙专家组顾问。
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时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他就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教育学会,并支持进步的学生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党的教育事业。1954 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以他为主要领导成员,组建成立了武汉水利学院(此后先后更名为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并成为首批全国重点大学。2000年,武汉水利电力大学与原武汉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和湖北医科大学合并组成新的武汉大学前,该学校已成为国内外水利电力领域著名的大学,为我国建设事业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水利电力方面的高级科技人才,推动和促进了我国水利电力事业的发展。根据我国自然条件的特点及经济建设的需要,他还在1958年创办了世界上唯一的河流泥沙及治河工程专业,并建设起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河流泥沙研究基地。
在三十多年的高校领导工作中,他8小时上班时间完全投入在办学和教育事业上,而把所有能利用的业余时间全部用在了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上。他善于抓主要矛盾,善于抓大事,把主要精力都花在党的教育事业上,同时又不放弃科研工作。他治学态度非常严谨。他既精通英、俄、德等外语,又具有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他在文字上的严格精炼是众所周知的。在科学研究中,他善于运用哲学思想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他在业务自传中写道:“从事业务工作,同干党的行政工作一样,指导思想如何是十分重要的。搞科学理论研究如此,解决重大技术问题也是如此。50年代我注意以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为主系统读了一些马、恩、列、斯的哲学著作,感到有如启蒙教育,受益匪浅,从思想深处深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事半功倍的锐利武器。”他常说:“如果一辈子想为人民多做点有益的事,就要一辈子学习辩证法”。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 年代,他编著的《水力学》和《河流动力学》等教科书中,既反映了当时国际学术水平,又纳入大量个人研究成果,其中许多精辟的论述和分析,无不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并以立论严谨、说理透彻而深受广大教学科研工作者的褒赞。
作为学校领导,对待下级和中青年知识分子,他循循善诱,言传身教。他培养的学生已遍布全国,桃李满天下。有的已成为国内外很有影响的专家教授,有的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更多的成为我国水利电力事业的中坚力量。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多次住院,行动非常不便。可是,他依靠药物的支持,利用每次服药后药物作用发挥的时间,主持会议,与人谈话,指导研究生,深入实验室,用颤抖的手写讲稿,编教材。仅论文和有关报告,就有30余万字。同时,他还频繁奔波于北京、南京、郑州、宜昌等地,参加各种重要会议。仅1981 年7月到1982年8月这段时间,出席全国性专业及有关会议共9次计100多天,还不包括他当时在校内所担任的党和行政工作。不说一个疾病缠身的老人,就是一个体格健壮的人,要完成这么多工作,没有一种拼搏精神,是不可能办到的。
(张小峰)
简 历
1917年1月15日 出生于湖北巴东。
1939年7月 毕业于武汉大学工学院。
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 中央大学工学院航空机械研究班学习。
1940年3月至1943年3月 中央水利实验处(重庆)先后任技佐、技士、副研究员。
1943年3—8月 恩施湖北省银行水利技术专员。
1943年9月至1944年1月 日寇进攻战事吃紧,辞职在家。
1944年2—7月 重庆乡村建设育才学院任水利科讲师。
1944年9月至1946年8月 国民政府水利委员会(重庆南京)任副工程师(在职期间曾考取公费留美,于1945年5 月出国,1946年7月回国)。
1946年8月至1947年10月 中央水利实验处(南京)研究员。
1947年11月至1954年11月 武汉大学教授,校副教务长、工学院副院
长、水利学院院长、校党组成员。
1954年11月至1978年10月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副院长、党委常委。
1978年10月至1983年10月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院长兼学院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主席。
1983年10月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名誉院长。
1998年12月21日 逝世于武汉。
主 要 论 著
1 张瑞瑾. 河流动力学. 北京:中国工业出版社,1961.
2 张瑞瑾. 河流泥沙动力学.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
3 Zhang Ruijin,Xie Jianheng. Sediment Research in China. 1992.
4 张瑞瑾. 黄河泥沙冲积数量之分析. 水利,1947,15(1).
5 张瑞瑾. 悬移泥沙在二度等速明流中的平衡情况下是怎样分布的. 新科学,1950(3).
6 张瑞瑾. 关于费里堪诺夫的明渠挟沙力流的重力理论. 武汉水利学院学报,1957(1).
7 张瑞瑾. 长江中下游水流挟沙力研究. 泥沙研究,1959,4(2).
8 张瑞瑾. 长江中下游水流挟沙力研究(续). 泥沙研究,1959,4(2).
9 张瑞瑾. 论重力理论兼论悬移质运动过程. 水利学报,1963(3).
10 张瑞瑾. 论环流结构与河道演变的关系. 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土木、建筑、水利版),1964(1).
11 张瑞瑾,等. 评爱因斯坦关于推移质运动的理论兼论推移质运动过程.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院报,1965(3-4).
12 张瑞瑾. 中国水利建设中的水文工作. 中国科学,1975(1).
13 张瑞瑾. 静水过船,动水冲沙.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报,1975(1).
14 张瑞瑾. 高含沙量水流流性初探.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报,1978(1).
15 张瑞瑾. 对黄河中游的认识.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报,1979(4).
16 张瑞瑾. 关于根治黄河的关键途径问题.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报,1979(4).
17 张瑞瑾. 关于河道挟沙水流比尺模型相似律问题.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报,1980(3).
18 张瑞瑾等. 蜿蜒型河段演变规律探讨//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上海:光华出版社,1980.
19 张瑞瑾.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泥沙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中国水利,1981(4).
20 Zhang Ruijin,Sediment Problems of the Gezhouba Water Control Project on the Yangtze River,Paper No. 001,Series of Research Reports—WIHEE,May 1982.
21 张瑞瑾,谢鉴衡. 葛洲坝枢纽坝区泥沙与河势规划问题//葛洲坝枢纽工程科技成果交流会文件,1981.
22 张瑞瑾,等. 论河道水流比尺模型变态问题//第二次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3.
23 张瑞瑾,陈济生,谢鉴衡. 三峡工程前阶段泥沙科研工作汇报提纲// 长江三峡工程泥沙研究文集. 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1989.
24 张瑞瑾. 张瑞瑾论文集.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6.